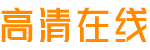隨著小米SU7價格發布,其訂單已經超過8萬臺,成為了目前行業的熱度之王。至此,中國市場中又多了一個新勢力,競爭壓力也不言而喻。

就在小米SU7發布的這幾天,大洋彼岸卻有一家新勢力被迫退市,生存情況艱難。不禁讓人疑問,為什么在這波智能化浪潮中,中國的新勢力還在不斷涌現,而美國新勢力中,除了特斯拉卻聽不到別家的聲量?
事實上,美國也有許多新勢力,并且十分被資本所看好,如本次退市的Fisker,此前市值曾高達79億美元,一度與Rivian和Lucid并稱為美國的“特斯拉殺手”,其創始人也有著寶馬、福特、特斯拉等多家企業工作經歷,而現如今卻宣告退市、資金困難,去年的交付量僅為4700輛,甚至不如一個中國二線新勢力一個月的交付量。

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本文開頭的小米,甚至是小鵬、理想、零跑、蔚來等新勢力,在這些中國企業看來,跨界造車好像是一件說干就干的事,但在美國則不同,除了Fisker外,仍有許多新勢力大面積倒下,有的甚至連車都沒交出來。
關鍵就在于,美國相比起中國,存在著去工業化的情況。
跌落神壇的特斯拉殺手
我們先來了解一下Fisker這家企業。簡單來說,就是一個汽車行業老兵的創業故事。
亨利克·菲斯克,知名汽車設計師,《007之黑日危機》中詹姆斯·邦德的寶馬Z8就出自他的手筆。除此之外,他還設計過阿斯頓馬丁的車型,并且做過特斯拉的設計顧問。

以上經歷,足以彰顯菲斯克的傳奇。或許是“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,做設計多年的菲斯克,萌生出了造車的想法。
2007年,新能源汽車的大潮還并未襲來,市場上的主流仍是燃油車。然而,此時的菲斯克卻仿佛洞察了大勢,創立了Fisker Automotive,創辦之初,菲斯克的目標便是制造出一款“可以與瑪莎拉蒂、阿斯頓馬丁媲美的新能源車”。
在四個月后的北美國際車展上,菲斯克便推出了豪華混動車Fisker Karma,對標特斯拉純電動跑車Roadster。

新車一經亮相,便引發了空前反響,畢竟在當時那個年代,這樣的汽車無論是設計理念,還是動力結構都足以稱得上超前,不僅比爾蓋茨、萊昂納多等大咖成為這款車的第一批用戶,《時代雜志》更是將其評選為年度汽車。
大咖背書、年度汽車榮譽等光環加持,資本融資也紛至沓來,其風頭一時無兩。用一句話概括,Fisker Karma是生在光環之下的。
2009年時,菲斯克拿到了美國能源部的5.29億美元貸款,條件是需要其在17個月內實現車型的交付。
然而,Fisker Karma最終卻倒在量產的魔咒中。注意“量產”這兩個字,在后文中會經常提到。
當時的Fisker Automotive面臨著三個方面的困境:量產難題無法解決,資金儲備也在日益下滑,有消息稱,其造出一輛Fisker Karma就要虧損3.5萬美元,可謂是燒錢不止。屋漏偏逢連夜雨,車輛的質量問題也隨之涌現,儀表盤、警示燈、車窗及收音機會出現間歇性故障。
此后,Fisker Automotive走上了貸款停止、資本退場、車輛召回、大規模裁員、公司破產的路,最終被萬向集團收購。
到了2016年,菲斯克再度進入汽車行業,新公司Fisker Inc誕生,似與過去揮手告別。

與上次創業不同的是,這次菲斯克沒有選擇對標阿斯頓馬丁、瑪莎拉蒂這樣的豪華車,而是選擇了將特斯拉當成最大的競爭對手。
其實這也很好理解,2016年時,新能源浪潮已經開始出現,中國新勢力開始破土而出,但尚不成熟,特斯拉幾乎就是當時的行業先驅,許多人都幻想著馬斯克“改變世界”的豪言壯語,將特斯拉當成最大的競爭對手。于是,純電動SUV Fisker Ocean誕生了,美國地區的售價為37499美元。
2020年10月,全新的Fisker借殼上市,股價一路大漲,Ocean的生產也已經定下計劃。難道說這回菲斯克要成功了嗎?

并沒有,同樣的量產問題這次依舊沒有解決,菲斯克在同一個地方,摔了兩個跟頭。
要知道,新Fisker采用的是輕資產的運營方式,雖然可以減少運營壓力,但其產量爬坡卻極其緩慢,質量問題也頻頻出現,在2023年,其交付量約為4700輛,甚至不如中國二線新勢力一個月的交付量。
在2024年3月初,Fisker宣布全面停產,并計劃大幅裁員,但股價暴跌的現象已經很難挽回,被許多人認為失敗或許已成定局。
美國新勢力,死于量產
從菲斯克的兩次創業中,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核心問題,那就是“量產”。
就比如本次的菲斯克,第二次創業時推出的Ocean,就曾因為法規認證時間、供應鏈問題被減產,第二款車型Pear的量產時間更是一再跳票。

誠然,汽車的外觀、產品力、能耗、價格等問題都與銷量密不可分,但這些更多是針對消費者層面,對于公司來說,能不能跨過“量產地獄”,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,Fisker的兩次失敗足以說明問題。
那么為何美國新勢力量產如此艱難?
在文章開頭提到,美國相對于中國,去工業化程度較高。這并不是說美國沒有工業化,相反美國還一直是全球制造強國,在全球5大的半導體產業中,有3家都在美國,在全球10大科學儀器儀表制造商中,美國常年占據6家以上,而在醫療器械領域里,美國更是制造的佼佼者。
在這些高端制造業上,美國從來就沒含糊過,但在低技術的制造業上,美國就一言難盡了。
就像是一條微笑曲線一樣,美國企業只管前端和后端,將研發、設計、銷售牢牢握在手里,如智能化技術、芯片設計等等,而至于低技術的制造,則可以交給墨西哥、東南亞等國家完成。

而我國則不同,加工、制造牢牢握在自己手里,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車領域,全球根本沒有國家能趕上。
比如說核心的電池技術,2023年全球十大動力電池裝機量企業中,中國占了6家,而美國并沒有企業上榜,而在正極材料、電解液、隔膜等領域,中國更是做到了世界領先。
這就給中國新能源汽車帶來了一個最核心的優勢,那就是生態。
有了生態,意味著在新能源車的研發、生產、制造等領域中國可以全包,造車的難度大幅度降低,如此多的跨界造車就是最好的證明。
其次,便是價格問題,供應鏈自主可控,意味著成本可以越來越低,車企有更多的空間去打價格戰,產業也會越來越卷,這也是國外車企沒有的優勢。
就比如此前日本專家拆解中國某電動車時,說日本也可以造出來,但成本會高很多,完全沒有中國車企有競爭力。
而美國也是如此。盡管美國一直在鼓勵創新,但低技術制造業卻越來越空心化,就像一個“大頭娃娃”,“四肢”越來越不聽使喚,整個供應鏈的脆弱性開始凸顯。
在這種情況下,一定要把供應鏈、產業鏈重新搭建起來,但難度可想而知,所以美國選擇將供應鏈制造環節直接遷移回來,瘋狂補足自己的缺陷。
從某種程度來看,中國也是如此,有著制造、加工方面的優勢,也在拼命補足兩頭的缺陷,致力于芯片、智能化技術等高端技術的研發。
所以,不是美國誕生不了成功的新勢力,而是這些新勢力根本沒辦法量產造車啊。自己造車,國內沒有生態,選擇代工,成本也下不來。
在這種情況下,想要破局只有一種辦法,那就是在中國建廠生產,特斯拉就是個最好例子。

我們都知道當年的馬斯克有多瘋狂,特斯拉的訂單有多火爆,但是這些訂單,就是生產不出來,在2017年到2019年年中,馬斯克都面臨著極大的產能壓力,甚至將那段時間稱作生產和物流的“地獄”。華爾街甚至悲觀預計,如果特斯拉在18個月內無法獲得大約80億美元的資金來為補齊營業虧損,那么該公司撐不過1年。
最終,特斯拉公司與上海市政府、上海臨港管委會簽署了純電動車項目投資協議,建設了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,特斯拉才算是幸免于難。

后面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,特斯拉就此騰飛,馬斯克也僅用了3年時間,身價便從2020年初的270億美元飆升到了2020年7月的705億美元,超越了股神巴菲特。5個月后,馬斯克身價超過比爾·蓋茨,成為全球第二大富豪。
到了2021年1月7日,馬斯克的個人凈資產升至1850億美元,超越了亞馬遜CEO杰夫·貝佐斯,成為全球第一富豪。
歸根結底,還是“量產”二字,就連特斯拉也擺脫不了這個“魔咒”,何況Fisker呢?
比賽還沒開始,美國新勢力就輸了
除了Fisker之外,其余兩家“特斯拉殺手”的情況也不容樂觀。
Rivian的賬面儲備至2023年底僅剩570億美元,兩年時間花光了102億美元,去年的交付量僅為2.03萬輛,同樣也出現了產品召回。
Lucid雖然緊抱中東土豪大腿,但2023年的營收也出現了下滑,盈利能力堪憂,在過去一年的交付量僅為4369輛。馬斯克曾表示,他們的沙特金主是唯一讓Lucid活下去的東西。
再看看中國的新勢力,大多已經跨越了量產地獄,主要問題還是外觀、產品力、性能、價格等等方面的競爭。
而美國新勢力,卻連最基礎的量產問題都無法解決,怎么可能再出現第二個特斯拉呢?
我們可以這樣思考一下,一家中國造車新勢力和一家美國新勢力,雖然雙方的產品力、價格都相差無幾,但中國新勢力卻能靠我國強大的制造能力、超強的產業生態、完善的供應鏈優勢,從成本和規模上徹底碾壓對手。
就像是在比賽還沒開始的時候,美國新勢力就已經徹底出局。